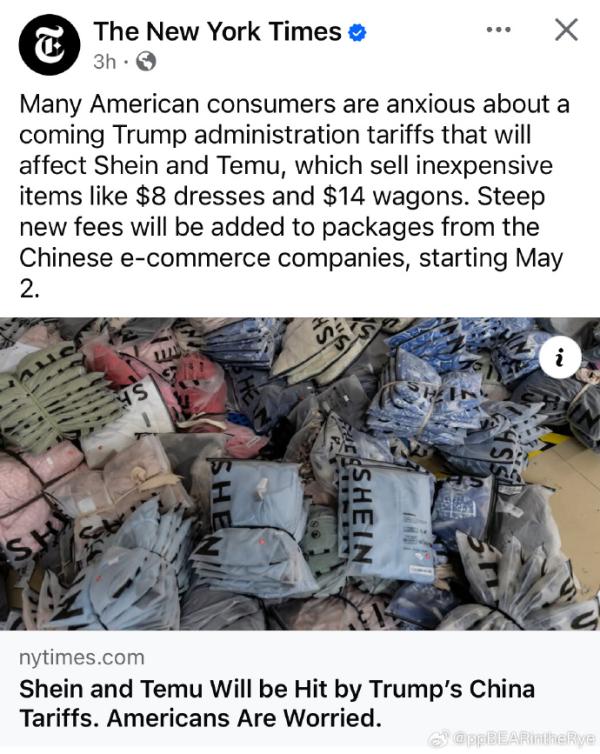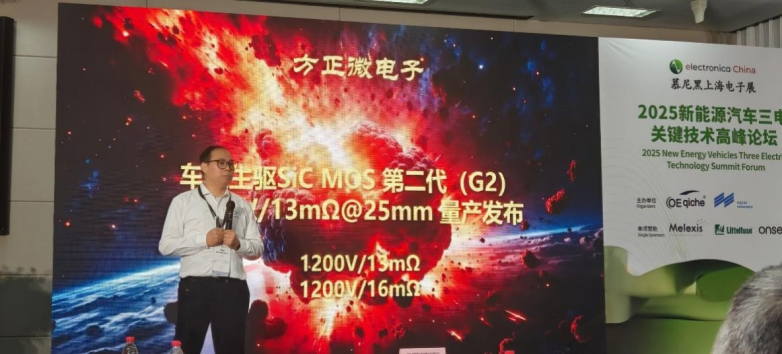2024年硅谷巨头想要的,以及他们误解的
【纵横网】硅谷是美国最引以为傲的成就之一,也是全球最强大的权力来源之一——一个创新和赚钱的引擎,让美国的盟友和对手都羡慕不已。
那么,如果硅谷真的掌管了一切——不仅仅是美国人与技术的关系,还有设定现代生活本身的条件会怎样?

有一种技术乐观主义的论点认为,硅谷而不是华盛顿的民选政府,是美国权力最好、最重要的面孔。政客杂志的总编辑马修·卡明斯基昨天写道,技术世界的自信活力与华盛顿的政治疲惫和悲观之间存在不讨人喜欢的差异:“我们对自己几乎没有信心。为什么其他人会有呢?”他严肃地问道。
他认为,许多人对华盛顿的不信任和缺乏信心可能会损害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这是一种病态,硅谷的态度提供了一个吸引人的解决方案。“西海岸权力的崛起与政治权力的衰落相吻合,”他写道。“政治是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对我们和世界其他地方来说,这种看法是丑陋的。如果美国从旧金山湾的视角来看是强大的,美国人当然不会这么认为。”
因此,如果硅谷的领导者是向世界展示果断、自信面孔的人——并且提出了一种新的领导美国实验的论点——那么值得更仔细地看看他们可能会引领它走向何方。
对科技行业的一个看法是,它倾向于自由派,以至于脱离了现实——一个充斥着年轻沿海精英、空洞的进步理想和对企业社会正义意识形态的奉献的行业。(这当然是埃隆·马斯克在购买推特公司时的看法,他将标志改为黑色X,并无情地戏弄其老高管。)
但有一种反应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货币和影响力。科技界一些最强大、政治上最直言不讳的人物(包括马斯克)最近与硅谷的企业自由主义决裂,转而支持右翼政治或彻头彻尾的阴谋论。
马斯克与右翼的暧昧关系有据可查,许多倾向于右翼的科技界人士开始类似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竞选活动的官方分支:马斯克的朋友、广受欢迎的“全力以赴”播客的主持人大卫·萨克斯现在据报道正在准备为特朗普可能的连任筹集资金(跟随一群在2020年做了同样事情的秘密硅谷投资者)。斯坦福大学培养的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的门徒布莱克·马斯特斯今年承诺在他的亚利桑那州第8国会选区竞选中提供“最好的美国优先代表”。
所有这些人(包括特朗普)有一个共同点:成功本身就是他们最大的名片。他们是亿万富翁,或者至少是千万富翁,他们的财富建立在创新、颠覆和精明投资上。他们向世界展示的面孔强烈暗示了他们的道路不仅是通往财富,而且是通往美国伟大复兴的道路。
通过创新实现伟大是硅谷的经典陈词滥调。技术理想主义的历史充满了突破停滞、创造一个由私人拥有的“新边疆”的渴望。
多年来,这些梦想跨越了意识形态的谱系。但随着它越来越多地与右翼的自由主义、反“觉醒”、创新第一的思想公开联系在一起,他们的修辞与创新如何反复改变世界的实际情况越来越奇怪地不一致。
帮助建立硅谷神话的创新——互联网、个人电脑、智能手机——每一个都是为了满足平凡、研究或消费者驱动的需求,而不是打破现状的自觉尝试。虽然互联网的发明是由乌托邦网络愿景家推动的,但它是由联邦政府委托的,目的是提高核指挥控制系统的韧性。一些决心打破IBM事实上的垄断的企业家德克萨斯州的野catters,主要归功于在每个家庭中放置一台电脑。最初的智能手机是黑莓手机,它是一个被美化的寻呼机。
硅谷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大规模政府投资的基础上的,在半导体行业、互联网、为风险投资提供税收优惠。其发明者及其产品主要在大学的安全范围内得到滋养(例如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安德烈森在那里开发了开创性的马赛克浏览器)。建造硅谷并充斥其起源故事的机智、足智多谋的人物,与当今科技先锋的屠龙宏伟相去甚远。
你从阅读安德烈森的“技术乐观主义宣言”中不会猜到这些,该宣言认为“敌人是那些在年轻时期充满活力、充满活力和寻求真理的机构,但现在已经被腐蚀和崩溃——在越来越绝望的尝试中阻碍进步,以继续相关性,疯狂地试图证明他们持续的资金尽管功能失调和无能不断升级。”
在其完整的历史背景下,像马斯克和安德烈森这样的主要推动者的英雄自由主义抱怨开始看起来不像是思想领导力,而更像是他们声称要扫除的确切类型的陈词滥调——一种由其赢家方便地重读历史的手法。
公平地说,他们的观点,即使在安德烈森最直接的意识形态对手中,几乎没有人——不同意美国某种程度上被困住了,我们对未来的集体愿景已经变得暗淡或完全消失了,需要改变一些事情。即使是人工智能的革命性承诺也可能不是救星:正如《纽约时报》的罗斯·多萨最近在一份涵盖安德烈森宣传的通讯中指出的那样,人工智能“可以更容易地将我们带入个性化幻觉、舒适麻木、模拟关系和精确引导的数字成瘾的未来,就像进入人工智能使艺术杰作、癌症治疗、自动驾驶汽车和火星探险成为可能的未来一样。”
硅谷当前对改变某事的狂热问题在于,几乎不可能预测这种变化的结果会是什么。将一台连接互联网的超级计算机放入几乎每个美国人手中的革命是多年来由临时修补、市场驱动的妥协和远见卓识的工程师的坚定奉献所导致的,而不是一个政治项目直接的结果。
这并不是说硅谷的潜在世界建设者不能实现他们改变的目标,只是这更经常是历史的意外。(而且,结果很难预测:硅谷的创新者创造了他们现在(可以理解地)谴责的社会问题,即智能手机及其伴随的数字生态系统,这主导了现代美国生活。)
毕竟,“快速行动,打破事物”是一个有效的口号,如果你的目标是推翻一个僵化的企业巨头,或者在创新产品上击败你的竞争对手。但它与世界建设的实际、混乱的业务直接对立——政治理论家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艰难地钻孔的硬木板”,一个项目,记住,“任何寻求这样做的人……必须冒着自己的灵魂风险。”变化不等于建设。
这至少应该冷却卡明斯基的忧郁沼泽生物所表达的嫉妒:科技界的鲁莽弗兰肯斯坦博士们,与他们劳动的成果一样,很可能会感到惊讶、失望,甚至被压倒,而不是在其中欢呼。
特别提醒:如果文章内容、图片、视频出现侵权问题,请与本站联系撤下相关作品。
风险提示:纵横网呈现的所有信息仅作为学习分享,不构成投资建议,一切投资操作信息不能作为投资依据。本网站所报道的文章资料、图片、数据等信息来源于互联网,仅供参考使用,相关侵权责任由信息来源第三方承担。
本文地址: